鄉村紀事:小蛋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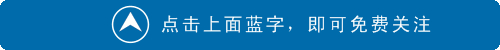
文:丁可
圖:來自網絡
小蛋是我的堂侄。娘生下他還沒聽清他的哭聲,就躺到黃土下去了。是姑媽抱走了他,像抱走一隻哼哼唧唧拱著找奶吃的小狗。姑媽以米湯麵糊餵養,好歹保住了他的一條命。
八九歲時,他才從姑媽家回來,爹給他隨便取了小蛋這個名字。此時的小蛋,比同齡的孩子都要矮小,眼還有些斜,皮膚黑黑的,乾乾巴巴,走動時,像一截木頭。

三年級還沒上完,小蛋就輟學了。印象中的小蛋寡言少語,近乎木訥。鄰家的孩子在一起扎堆嬉鬧,小蛋只在一邊怯怯地看。我從未聽到過他的喊叫,甚至一句完整的話。我曾在一首詩裡這樣說他:貧窮的苦孩子,說話聲音也小,像小蟲子叫。
十二三歲開始,小蛋跟著爹學剃頭。去鄰村,爹一頭挑著爐子,一頭挑著凳子和盆在前面走,小蛋提著裝有剃頭刀具的小木箱,一聲不響地跟在後面。爹去世後,剃頭挑子就落到了小蛋的肩上。鄰村一百多個男人的頭,小蛋每月挨個撫摸一次,換來些糧食餬口。
他的眼不大得力,修理頭顱時,要湊近了看,更像把人家的腦袋抱在懷裡。村人喜歡蹲在他的周圍拉呱兒,高一聲,低一聲,天南海北,談鬼說人。小蛋只是默默地幹活,從不插言。
以為小蛋就這樣窩窩囊囊,低眉順眼地打發一生了吧。像許多村民那樣,活一輩子,除了喚狗吆鵝,喝斥兒女大些聲音,更多的時候,只是木木地聽別人訓話或者不明不白跟著喊幾句口號。從未想獨出機杼,讓聲名遠播。從未想能登高一呼,從者如雲。
侍弄莊稼悄無聲息,牽著牛羊一聲不吭,身子骨疼了,低聲呻吟。只有白菜蘿蔔聽到,飯碗聽到,農具聽到。年關放一掛鞭炮,是他們鬧騰出來的最大的動靜。草木一秋啊,風吹簌簌,春去秋來啊,鴨言雀語。喉頭還沒怎麼舒展過,就躺成黃土下永遠的寂靜。
我沒有想到小蛋響亮的聲音,這幾年竟成了村上的主旋律。
放下剃頭挑子,小蛋在村裡路邊開起了商店。商店面積不過二十多個平方,石棉瓦搭頂。貼牆用磚頭壘成的貨架上,擺上生活日用品。櫃檯左右,牆角旮旯,堆著從集市上批發來的各類蔬菜。

為了大造聲勢,小蛋在商店後面的大榆樹上安裝了兩個高音喇叭。每天黎明,小蛋就像公雞打鳴,先是對著話筒噗噗吹上兩口,接著就開始“報曉”:“喂,喂!丁榮沛商店,有剛起來的豆芽、 茄子、黃瓜、啤酒、海南島的南瓜,還有各種新鮮小菜。手工饅頭,絕對好吃,絕對好吃。”吆喝一陣,放一段歌聲,之後再反覆吆喝。
小蛋的貨賣得便宜,秤又給得夠,村人紛紛向他的聲音裡聚攏。
生意越做越紅火的小蛋,娶上了媳婦,有了兒子,又買了一輛摩托三輪。他的吆喝聲底氣更足,新詞兒也多了。有時,在小蛋演說的間隙,兒子小小蛋也學著爸爸的口氣,稚聲稚氣地客串一番。小小蛋咬字不準,把“絕對好吃”,說成“絕對好詩”。
幾天前,我回故鄉去。離村子老遠,就聽到了小蛋的聲音。極富煽情的如數家珍的商品介紹,有板有眼,字正腔圓。
這就是多年前那個木頭疙瘩似的小蛋嗎?是苦寒的往日裡那個囁嚅不敢言不能言的小蛋嗎?我為小蛋奔放自如的聲音而高興。他的聲音是穿透多種屏障的一種精神釋放,是自信之後放鬆之後的一種聲情拓展。我不想去糾正小蛋廣告語中的病句,那樣會使他興致勃勃的抒發有所顧慮。就讓小蛋保持著自己聲音的毛角毛稜吧。

我下了自行車,邊走邊仔細傾聽著,像村前村後的楊柳,張著春風盪漾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