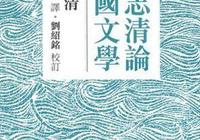1955年的夏濟安(右)、夏志清
從2015年開始,由夏志清夫人王洞女士主編,蘇州大學文學院季進教授編注的五卷本《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以下簡稱《書信集》)陸續推出繁體中文版,迄今已經問世三卷。而今年,卷一(1947—1950)的簡體中文版也由“活字文化”推出。至此,漢語讀者就都有機會見到這部卷帙宏富的《書信集》了。近日,本報特約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就夏氏兄弟及他們之間的通信對恰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問教授任上的陳國球(左圖)進行訪談。
陳國球畢業於香港大學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現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與香港人文學院創院院士。著有《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抒情中國論》與《香港的抒情史》等,編有《文學史》集刊(與陳平原教授合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與王德威教授合編)與《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主編,共十二卷)等。
《書信集》再現了夏氏兄弟學術訓練的整個過程
李浴洋:1940年代後期,夏濟安、夏志清兄弟二人都曾在北大任教。在某種程度上,北大可以說是他們學術生涯的起點。我們今天也在這裡探討他們之間的書信。在您看來,《書信集》面世的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陳國球:我想,《書信集》出版的意義至少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個角度來講。首先,就個體層面而言,其中記錄了兩位重要的華人學者——夏濟安、夏志清兄弟二人在1947至1965年間對於人生道路、現實世界與知識世界的探索。他們就這些方面的話題進行的交流,很多是隻可能在相互信賴的親密無間的兩個個體之間展開的。而在他們通過書信展開交流的十七年間,正是中國歷史、政治、文化與社會發生巨大變動的年代。他們兄弟二人的足跡先後經歷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地區與北美,在冷戰背景下,他們在當時做出的觀察、反應、思考與選擇,自然也就可以為我們更好地認識與理解那個時代提供某種參照。因此,無論是從個體角度來說,還是從“時”、從“地”的意義上看,《書信集》都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文獻。
除去內容方面,《書信集》在形式上也自有其意義。“書信”這一體裁的歷史非常久遠,在中國文學史與學術史上原本就有通過書信表達判斷與互動的傳統。但我們讀到古人的書信,大都是通過他們的文集。也就是說,這些書信已經經過了人為的選擇,是一種單向的表達。但《書信集》中收錄的夏氏兄弟的書信卻是它們的本來面目,這是非常難得的。
李浴洋:我注意到,夏志清最後的學術工作幾乎都與“書信”有關。根據王洞女士的介紹,在他2009年首次病危時,最為掛懷的事業便是希望可以將他與張愛玲以及夏濟安的書信整理出版。經過他歷時三年的努力,《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於2012年問世。次年,夏志清去世。在他身後,王洞女士秉承他的遺願,開始與季進教授一道編注《書信集》。參照一些與他晚年有過交往的學者的回憶文章可知,為了這兩種“書信集”,他基本上投入了自己最後的全部精力,甚至為此擱置了一些系統整理個人學術著述的提議。您如何看待他的這一選擇?
陳國球:夏志清晚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書信整理中,與他最後一個人生階段的生活狀態有關。1991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從1992年開始,他基本上就沒有再做大型的學術工作了。夏志清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三種,即他的三部英文專書與論文集:一是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二是196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三是2004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收錄了他在哥大任教期間的16篇重要論文的《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所有這些,都是他在退休以前完成的。此外,他還有一些中文著作,編選過兩種中國文學英譯的大學教材。但最重要的便是這三本,而他的學術地位,也正是通過這三本著作建立起來的。夏志清是很有信心的學人,他相信這三部著作已經足以使他“不朽”了。因此,在退休以後,他便進入了另外一種生活狀態。在我看來,他在最後一個人生階段所做的其實是一種對於人生經歷與學術道路的“回顧”。
夏志清對於書信的整理,便是一種“回顧”。在他的生命中,與張愛玲以及夏濟安的音問交流無疑是兩段非常重要的經歷。張愛玲是他最欣賞的中國作家,夏濟安則是他在生活與學術上最信賴的兄長。當然,《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與《書信集》也有不同。在前者中,“主角”是張愛玲;而在後者中,“主角”則更多是夏志清自己。所以,對於瞭解夏志清的生命史而言,更重要的應當還是《書信集》。
《書信集》的出版說明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對於往來書信都有十分精心的保管。保存下來的612封書信儘管不是他們的全部通信,但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他們當初應當完全沒有考慮過會在日後將通信發表,所以這一行為說明了他們原本就視彼此的通信為個人生命的重要記錄。是故,《書信集》的出版承載的也就更有一種“回顧”的意義了,因為其中記錄的是他們的真實足跡。雖然夏志清生前只整理完成了張愛玲給他的信件部分,但我相信王洞女士執行的正是他的思路與追求。

年輕時的夏志清(右)與哥哥夏濟安。
李浴洋:《書信集》繁體中文版面世後,引起不少反響。審讀過卷一書稿的王德威教授在《後記》中指出:“(夏濟安、夏志清)兩人在信中言無不盡,甚至不避私密慾望。那樣真切的互動不僅洋溢著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間的信任,應是書信集最珍貴的部分。”那麼,《書信集》中最讓您感興趣的部分是什麼?
陳國球:我是2015年在臺北出席“中研院”舉辦的“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前夕,首次讀到《書信集》卷一的。記得當時的會議日程非常緊張,我利用一個晚上的時間把卷一翻了一遍。因為那次會議兼有“紀念”性質,又適逢卷一首發,所以大家在討論《書信集》時,更多關注的自然都是與夏志清的人生經歷有關的內容,還有一些“八卦”。而我在翻的時候目標卻非常單一,就是去看其中學術性的部分——具體而言,便是夏濟安與夏志清的讀書心得。以往我們對於他們兄弟二人的最初印象,便是他們編輯雜誌、從事翻譯、寫作專書與引發辯論,好像他們一出手便是十分成熟的學者。但在《書信集》中,我們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讀書軌轍,包括他們最早讀的是什麼書,如何從一本書讀到另一本書,他們在讀書過程中如何轉變與更新他們的書單,以及他們就一些學人與學術著作所做的臧否,等等。換句話說,《書信集》再現了他們整個學術訓練的過程。在我看來,這是其中很有意義的部分。
以夏志清為例。我們此前能夠讀到的他最早的學術著作便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但通過《書信集》,我們可以知道,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小說”其實並非他長期關注的對象。他在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前所受的學術訓練幾乎都是關於詩歌研究的。特別是在英國詩歌研究方面,他投入了很多精力。他在耶魯攻讀的便是英國文學博士課程,博士論文正是關於英詩的。那麼,他的學術興趣是如何從英詩轉向中國小說,在這一轉向過程中,他有哪些“變”,又有哪些“不變”,這就值得我們去思考了。
我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儘管有文學史的眼光,但主要還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夏志清所完成的是一項在歷史向度上的文學批評實踐。這應當是我們對於《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基本定位。而他之所以會這樣研究“中國現代小說”,與他此前所受的學術訓練直接相關。也就是說,在他對於“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中,其實貫徹了許多英詩研究的方法。所有對於這部著作的討論,都應當首先回到這一“起點”上。在《書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學術成長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我閱讀《書信集》,關注的正是學者的成長史。

夏志清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但隨著時日推移、教學相長,他對現代中國的文學與歷史愈加同情與肯定
李浴洋:這就說到您在《“文學科學”與“文學批評”——普實克與夏志清的“文學史”辯論》一文中,曾經對夏志清的文學觀念的形成詳加考證。您認為他在寫作成名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其出發點固然是‘新批評’的文本中心論,但終點卻是滿懷道德熱誠的利維斯‘偉大的傳統’觀”。強調夏志清在燕卜蓀、蘭色姆與布魯克斯之外,還受到了利維斯的深刻影響,是您的重要創見。在《書信集》中,您是否又發現了更多可以豐富與補充這一命題的材料與線索?
陳國球:事實上,夏志清在1978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序裡就提到自己受到利維斯《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的影響。在閱讀《書信集》時,我的確留意過夏志清是從何時開始接觸利維斯《偉大的傳統》的。其實他閱讀利維斯很早。在2002年發表的《耶魯三年半》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早在上海期間就已經看過利維斯的《英國詩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與《重新評價:英國詩歌的傳統與發展》(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書信集》可以印證這個說法,從中我們更清楚地知道他是比較晚才接觸專門談小說的《偉大的傳統》,當然這本書也要到1948年才出版。
利維斯是劍橋文學批評學派的關鍵人物。而這一學派的其他代表,像瑞恰慈與燕卜蓀,都對同一時期的中國文壇產生過很大影響。他們基本都是做詩歌研究的,所以夏志清的學術之路也是從新批評到利維斯的英詩研究。
夏志清是在耶魯讀書期間開始涉獵小說研究的。《書信集》記錄了他在耶魯修過一門小說研究的課程。而他讀《偉大的傳統》,便是為了應付這門課,這時已是他的博士課程的後期。可以說,夏志清的文學觀念正是在這一從英詩到英國小說的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此後,他寫作博士論文以及初任教職時,仍然都是以英詩為主。但當他著手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時,他受到的《偉大的傳統》的影響便浮現了出來。
不過,就像我剛才談到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主要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在夏志清寫作時,他做的主要工作還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對小說文本做出判斷,以此去發現他眼中的“好的作品”。我說《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受到《偉大的傳統》的影響,可以聯繫到他提出的“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又譯“感時憂國”)的觀點。但必須說明的是,在1961年出版的《小說史》第一版中,夏志清並未提出這一看法。在1971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中,他才加入了《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包袱》(“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這篇著名的論文作為附錄,同時作為全書的“主線”。由此可見,夏志清的文學觀念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髮展的。起初,他考慮最多的應當是“文學批評”本身的標準,即一部作品“好”還是“不好”,它的結構如何,它的技藝,等等。但在研究過程中,他開始考慮一部作品在“文學批評”以外的意義了,例如對於人生的意義,對於社會的意義,對於民族國家的意義,等等。因此,他才會把“情迷中國”的說法補充進來。而《書信集》記錄的便是他的這一思考過程,這對於我們更為準確地理解夏志清的文學觀念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陳國球
李浴洋:您對於夏志清的文學觀念的理解似乎與學界的普遍認識有所不同。對於他提出的最具影響的“Obsession with China”的概念,您不同意通行的“感時憂國”的譯法,主張應當譯為“情迷中國”。而您也將自己的一部文集命名為《情迷家國》。這讓我對於兩者之間的關聯不由產生了興趣。能否請您解釋一下您主張把“感時憂國”改譯為“情迷中國”的理由,並且談一談您對於夏志清的這一提法的看法?
陳國球:《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是由劉紹銘先生等人據原著第二版翻譯,於1979年最先在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的。這一中譯本已經收錄了《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包袱》一文。該文由丁福祥與潘銘燊兩位先生翻譯,題目改作《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譯筆流暢通順,但也犧牲了許多原文的深義。自此以後,“感時憂國”一說,便不脛而走。我最早閱讀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版本,就是這一中譯本。我對於“感時憂國”的瞭解,也是從此開始的。
後來我看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英文本,發現夏志清使用的原文是“Obsession with China”。 “Obsession”一詞在英文中包含有比較複雜的感情,但“感時憂國”就完全是歌頌愛國精神的正面意思了。這就啟發我重讀了《中國現代小說史》。我發現,在夏志清那裡,“obsession”顯然不是完全正面的。他講“Obsession with China”,有一種認為絕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都把自己的感情過於陷溺在對於中國的迷思當中的意思。而在他的整個論述中,得到更高評價的明顯是那些可以從對於民族國家的迷思中超越出來的作家。他認為這種對於中國的迷思,已經成為了絕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的一種包袱。他說“obsession”,是帶有批判性的。如果結合夏志清的文學觀念進行理解,他的這一態度也就更加明確。他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也是一位人文主義批評家。在他那裡,民族國家並不是最高的評價標準。他更看重的是對於人性與社會的關懷,是對於道德的反思與追問。而在他眼中,絕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並沒有做到這點。因此,我認為把“Obsession with China”翻譯為“感時憂國”是不夠妥當的,至少是不盡貼合夏志清的原意的。“情迷中國”的譯法或許好一些。
在寫作《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包袱》時,夏志清的基本看法是“情”代表了對於中國的付出,而“迷”則說明了這種付出是陷溺其間——換句話說,也就是缺乏批判性的。夏志清這樣說,並不是主張不要付出,而是強調付出必須以清醒的思考為前提,同時最好也具有某種超越性的關懷。這大致可以反映他本人的文化與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他的這一立場後來發生了變化。他自己做到超越民族國家了嗎?我認為沒有。非但沒有,而且隨著時日推移、教學相長,他更沉潛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體味與省思。
例如,1979年他在臺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過一本中文論文集《新文學的傳統》。在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時,他是站在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的視野中打量“中國現代小說”的;而到了《新文學的傳統》結集的時期,他雖然仍舊堅持人文主義的立場,但對於“新文學的傳統”本身卻多了一些同情,少了一些批判。他更加肯定“新文學的傳統”所具有的正面價值,欣賞富有人道主義精神、肯為老百姓說話而絕不同黑暗勢力妥協的新文學作家。
而在他轉向對於“新文學的傳統”加以肯定的背後,是他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變化。正如在“偉大的傳統”背後包含的是對於一個“文化傳統”的肯定,在夏志清眼中,中國同樣也有一個“偉大的文化傳統”——入世、關注人生,富仁愛精神。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這點並不突出。但在他的後期著作中,他屢屢表示對《詩經》、古樂府、杜甫、關漢卿等人作品的重視和珍惜。事實上他本身就是“情迷中國”的一員。我想,夏志清的這一變化與他的人生閱歷有關。儘管他十分強調文學的道德承擔,並且認為道德承擔與對於民族國家的承擔之間保有某種張力,但對於後者,他也沒法輕輕放下。隨著他經歷不同的人、事、時、地,他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思考,對於現代中國的文學與歷史也就愈加同情與肯定。

夏氏兄弟、宋淇、吳興華等人構成了一個鬆散的知識社群
李浴洋:您與夏志清的交往多嗎?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相關情況?您眼中的夏志清,又是怎樣的?
陳國球:夏志清的成就很高,爭議也很大。但無論如何,他都是一位有眼光的文學評論家,他有他獨到的觀點,而在他的觀點背後有一整套的理論資源。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他做出的具體判斷,這些都是應當承認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他的著作比他的辯論文章更精彩,他的著作帶給了我很多思考。
我與夏志清先生的交往並不多,印象中直接接觸只有兩次。一次是2000年夏先生來香港參加 “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有機會向他當面請益。還有一次是2005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夏氏昆仲與中國文學”學術會議提交《情迷中國》的論文,他來聽會,我們也有過面對面交流。除去這兩次,好像就沒有再見過面了。但我讀夏先生的文章著述,則早在1970年代開始。夏志清的中文文章,很早就從臺灣地區傳入香港;我在大學階段常置案前。後來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部分章節的中譯在《明報月刊》上發表,我也跟著讀。出書以後,我在第一時間就買了。再後來,他成為我的研究對象,我自然也就把能夠找到的他的中英文作品都讀了。我的感覺是他的英文非常漂亮,文體莊重而典雅,而他的中文則十分輕快,活潑而靈動。他的英文是標準的學術語言,主要面向學術界發言,而中文則俏皮一些,更容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我對於夏先生的印象,基本都是從閱讀中得來的。
在我眼中,夏志清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無論對於學術,還是世事,他都有很強的洞察能力。但我們對夏志清的瞭解,其實還是非常不夠。以他的學術而言,其中還有很多內容是我們並不清楚的。例如,有人認為夏志清不懂中國古典詩歌,事實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為研究生開的三門課,首先就是講“唐詩宋詞”。經多年累積,他在這範疇下的功夫不會少。可是至今未見有他的正式論述流傳,我們只能在《夏志清論中國文學》看到他的一部分比較負面的批評意見。但我注意到,1956年陳世驤赴臺講學,講的就是關於中國古典詩歌的話題。夏志清起初對於他的學術不怎麼恭維。這在《書信集》中就有記錄。但後來夏志清對於陳世驤的研究評價非常正面;陳世驤去世以後,他還專門寫作了紀念文章,文中說自己對中國的經史子集讀得遠不如陳世驤多。這一變化究竟如何發生?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李浴洋: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部少有的在海內外學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引發巨大爭議)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去年我訪問文學史家吳福輝先生時,他曾提到北大學人對於這部著作的最早接觸,便是得力於1970年代末期香港學生的私下攜入。香港與夏氏兄弟彷彿具有一種
特殊的學術因緣。除去吳先生談及的這段往事,夏氏兄弟的著作中譯本很多也都是在香港面世,並且經由香港對我們產生影響的。夏志清的好友宋淇長期旅居香港。而您也一直在香港工作、生活,能否請您談一談夏氏兄弟其人其書在香港的傳播情況,以及在您看來,在香港閱讀他們的著作,是否具有某種獨特的體驗與感受?
陳國球:香港學界對於夏志清的關注,絲毫不亞於臺灣學界。剛才已經談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最早是在香港出版的。此後,夏志清也有很多著作在香港流傳。他的著作在香港影響很大。例如,張愛玲雖然曾經在香港駐足,但香港學界真正開始關注她,還是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以後。再如,香港的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撰寫《中國新文學史》,頗有參酌《明報月刊》上夏志清的《小說史》中譯。至於後來夏志清苛評司馬長風之作,兩人因而筆戰,則是後話了。夏志清又有《印象的組合》一書,由香港文壇重鎮劉以鬯負責編輯。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更全面整理夏氏昆仲的著作,不少英文著述有了新譯,相信對學界又有新的影響。香港是一個重要的學術中介。你談到吳福輝先生的回憶,應當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不僅北大學人通過香港開始接觸夏志清的著作,上海的陳思和與王曉明兩位先生也曾經告訴我,他們最早閱讀的夏志清的著作也是從香港傳入的。
當然,談論夏氏兄弟與香港的學術因緣,如果僅從著作傳播的層面上立論,恐怕不免太過簡單。夏志清和他哥哥夏濟安與宋淇的關係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入口。兄弟二人在上海讀書時,就認識宋淇了。而他們之間的交誼,一直延續了數十年。因此,我讀《書信集》時很關心他們是怎麼講宋淇的。宋淇與他們的關係絕不是“好友”二字可以完全概括的。

無論是從個體角度來說,還是從“時”、從“地”的意義上看,《書信集》都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文獻。
他們三人之間有許多批評,但也有很多鼓勵,更有對於各自的人生道路的實實在在的幫助。比如,夏濟安在香港時期的生活問題,就有很多是宋淇利用他在美新社的身份幫忙解決的。他到臺灣以後,宋淇也繼續支持他的文學事業,為他的《文學雜誌》組稿。與此同時,夏氏兄弟對於宋淇的工作也經常施以援手。我注意到,宋淇在1961年出版過一本《美國文學批評選》。儘管這一選本的編者署名“林以亮”(宋淇筆名),但我相信夏志清為此也下了很大功夫,因為通過選目,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介紹的文學批評的觀念許多都是當時耶魯大學流行的,而這無疑是夏志清為宋淇提供的資訊。他們“合作”的這一選本不僅對於我們瞭解夏氏兄弟與宋淇的交誼很有意義,而且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夏志清在耶魯所受的學術訓練。
李浴洋:提及宋淇,便不能不說到今年同樣也有一部與他相關的“書信集”問世,那便是吳興華的《風吹在水上:致宋淇書信集》。我知道,吳興華是您很感興趣的學術對象。他與宋淇的通信是在1940至1952年間進行的。這與夏氏兄弟的通信時段(1947—1965)恰有部分重合,而相近的時代背景與人生經歷也讓這兩部“通信集”中的話題多有關聯。將兩者對讀,或許不失為一種策略。您對於兩者都做過專門研究,不知是否有什麼發現?
陳國球:你的思路很好。我在看他們四人的文章時,也想到應當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思考。通過他們的書信與回憶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在上海時期,宋淇與夏濟安曾經是校友,他們合辦過文學雜誌。宋淇常去夏濟安家中,有時夏濟安不在,他就與當時還是高中生的夏志清交談,夏志清很多關於英國詩歌的知識,都是通過宋淇瞭解到的。而宋淇與吳興華是燕京大學的同學,經由這層關係,夏氏兄弟也很早便知道了吳興華。無論是宋淇與吳興華,還是宋淇與夏氏兄弟,他們之間都是相互欣賞的。夏、宋、吳等又與其他背景及興趣相似的學人,構成了一個鬆散的知識社群。當時上海出版的《西洋文學》雜誌,便是以他們為主力。夏濟安與吳興華經常給這家雜誌投稿,宋淇更是串連京滬兩地作者的聯絡人。順帶一提,雜誌的編輯之一是柳存仁,這位蜚聲國際的漢學家曾幾度在香港居停,對香港的文化和教育都有過重要的影響。
《西洋文學》非常精彩。後來夏濟安到臺灣以後重辦《文學雜誌》,其淵源一是朱光潛辦過的《文學雜誌》,另外一個便是《西洋文學》。1952年之後,吳興華與宋淇書信斷絕,但他的作品卻開始以“樑文星”為筆名在臺灣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吳興華本人對此應當並不知情,這是出自十分欣賞他的宋淇與夏濟安的好意,他們有意把吳興華的文學火種播撒到香港與臺灣地區。而“樑文星”在當年的確也成為了港臺文壇上風靡一時的人物。